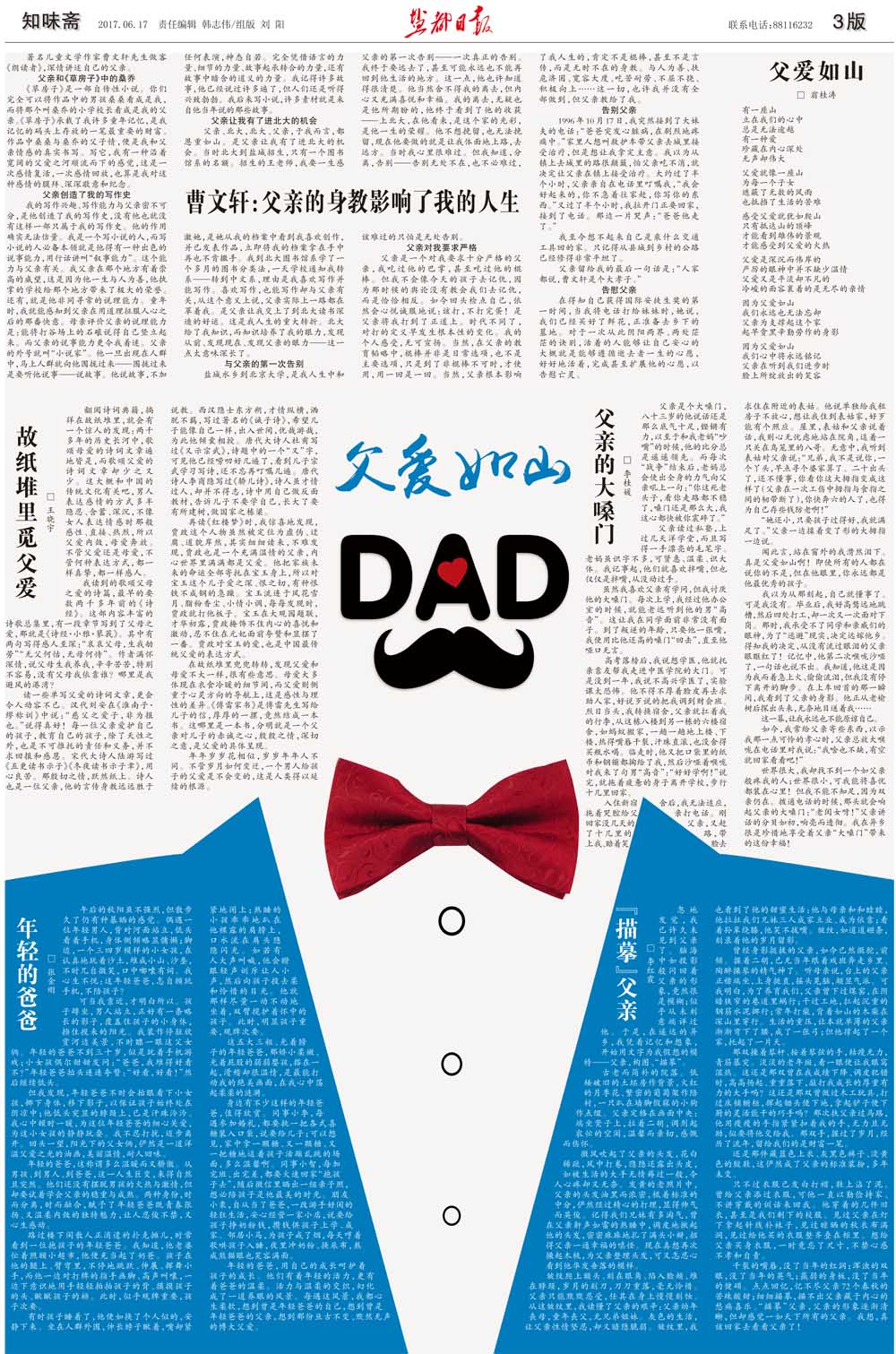内容详情
2017年06月17日
曹文轩:父亲的身教影响了我的人生
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先生做客《朗读者》,深情讲述自己的父亲。
父亲和《草房子》中的桑乔
《草房子》是一部自传性小说。你们完全可以将作品中的男孩桑桑看成是我,而将那个叫桑乔的小学校长看成是我的父亲。《草房子》承载了我许多童年记忆,是我记忆的码头上存放的一笔最重要的财富。作品中桑桑与桑乔的父子情,便是我和父亲情感的真实书写。写它,我有一种沿着宽阔的父爱之河顺流而下的感觉,这是一次感情复活,一次感情回放,也算是我对这种感情的膜拜、深深敬意和纪念。
父亲创造了我的写作史
我的写作兴趣、写作能力与父亲密不可分,是他创造了我的写作史,没有他也就没有这样一部只属于我的写作史。他的作用确实无法估量。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,而写小说的人必备本领就是他得有一种出色的说事能力,用行话讲叫“叙事能力”。这个能力与父亲有关。我父亲在那个地方有着崇高的威望,这是因为他一生与人为善,他执掌的学校给那个地方带来了极大的荣誉。还有,就是他非同寻常的说理能力。童年时,我就能感知到父亲在用道理征服人心之后的那番快意。母亲评价父亲的说理能力是:能将打谷场上的石磙说得自己竖立起来。而父亲的说事能力更令我着迷。父亲的外号就叫“小说家”。他一旦出现在人群中,马上人群就向他围拢过来——围拢过来是要听他说事——说故事。他说故事,不加任何表演,神态自若。完全凭借语言的力量、细节的力量、故事起承转合的力量,还有故事中暗含的道义的力量。我记得许多故事,他已经说过许多遍了,但人们还是听得兴致勃勃。我后来写小说,许多素材就是来自他当年说的那些故事。
父亲让我有了进北大的机会
父亲、北大,北大、父亲,于我而言,都恩重如山。是父亲让我有了进北大的机会。当时北大到盐城招生,只有一个图书馆系的名额。招生的王老师,我要一生感激她,是她从我的档案中看到我喜欢创作,并已发表作品,立即将我的档案拿在手中再也不肯撒手。我到北大图书馆系学了一个多月的图书分类法,一天学校通知我转系——转到中文系,理由是我喜欢写作并能写作。喜欢写作,也能写作却与父亲有关,从这个意义上说,父亲实际上一路都在罩着我。是父亲让我交上了到北大读书深造的好运。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。北大给了我知识,而知识培养了我的眼力,发现从前、发现现在、发现父亲的眼力——这一点太意味深长了。
与父亲的第一次告别
盐城水乡到北京大学,是我人生中和父亲的第一次告别——一次真正的告别。我终于要远去了,甚至可能永远也不能再回到他生活的地方。这一点,他也许知道得很清楚。他当然舍不得我的离去,但内心又充满喜悦和幸福。我的离去,无疑也是他所期盼的,他终于看到了他的收获——上北大,在他看来,是这个家的光彩,是他一生的荣耀。他不想挽留,也无法挽留,现在他要做的就是让我体面地上路,去远方。当时我心里很难过。但我知道,分离,告别——告别无处不在,也不必难过,该难过的只怕是无处告别。
父亲对我要求严格
父亲是一个对我要求十分严格的父亲,我吃过他的巴掌,甚至吃过他的棍棒。但我不会像今天的孩子去记仇,因为那时候的舆论没有教会我们去记仇,而是恰恰相反。如今回头检点自己,依然会心悦诚服地说:该打,不打完蛋!是父亲将我打到了正道上。时代不同了,对打的定义早发生根本性的变化。我的个人感受,无可宣扬。当然,在父亲的教育韬略中,棍棒并非是日常选项,也不是主要选项,只是到了非棍棒不可时,才使用,用一回是一回。当然,父亲根本影响了我人生的,肯定不是棍棒,甚至不是言传,而是无时不在的身教。与人为善、扶危济困、宽容大度、吃苦耐劳、不屈不挠、积极向上……这一切,也许我并没有全部做到,但父亲教给了我。
告别父亲
1996年10月17日,我突然接到了大妹夫的电话:“爸爸突发心脏病,在剧烈地疼痛中。”家里人想叫救护车带父亲去城里接受治疗,但是想让我拿定主意。我以为从镇上去城里的路很颠簸,怕父亲吃不消,就决定让父亲在镇上接受治疗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,父亲亲自在电话里叮嘱我,“我会好起来的,你不急着往家赶,你写你的东西。”又过了半个小时,我拉开门正要回家,接到了电话。那边一片哭声:“爸爸他走了。”
我至今想不起来自己是乘什么交通工具回的家。只记得从县城到乡村的公路已经修得非常平坦了。
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人家都说,曹文轩是个大孝子。”
告慰父亲
在得知自己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第一时间,当我将电话打给妹妹时,她说,我们已经买好了鲜花,正准备去乡下的墓地。对于一次从此阴阳两界、两处茫茫的诀别,活着的人能够让自己安心的大概就是能够遵循逝去者一生的心愿,好好地活着,完成甚至扩展他的心愿,以告慰亡灵。